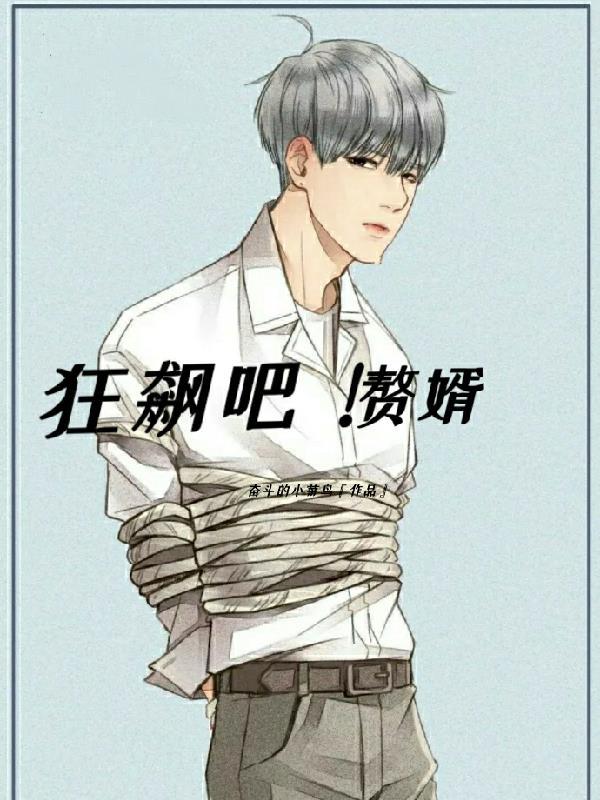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四十章(第1页)
张申最近很郁闷,景星走了,文学社散了,刚刚成亲的他很是烦恼“新人是当地的书香门第大户人家,长得端庄娴淑,琴棋书画样样拿得出手,看来从小在家没少念书。可相处一段时间下来,就蛮不是那么回事儿,脾性相差甚远。婆姨知书达礼,重点在达礼二字上。婆姨特别守规矩,跟她讲新女性的解放,她不屑一顾地说什么,夫妻一体,相敬如宾,三从四德,天经地义,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是扰乱人心有毒的东西,还劝我往后少看、慎看。一通道理讲得那是有理有据,叫人无可辩驳,无话可说,无可应答。”脸红脖子粗的他从此敬而远之,没了谈心、交心的欲念“真是念书不知书,不如不念书,知礼守死礼,不如不知礼。这女人念书念傻了,已经无可救药。可能在她眼里,我就是一误入歧途的狂生吧。”
张申很怀念过去的快活时光,常邀三五好友聚一聚,谈谈时事,论论时政,顺便邀几篇好文章,给他的报纸添添彩。当然他最想见的就是女人,这就是他心目中活生生的新女性,无论人还是才,那都是圈里的其他人没法比的。他也不晓得为甚婆姨同样生在这个时代,想的却天差地别,仿佛是生活在两个世界的人。张申想可能是女人在天津生活过一段时间见过世面的缘故吧。他有样学样,带着婆姨去了一趟西安,每日带着婆姨出双入对,参加各式二样社团聚会。世异时移,如今抗战时期的西安,跟抗战以前的天津已经不可同日可比,今非昔比不说,气氛也有些沉闷,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颓废复古的味道。婆姨跟他去了几次,开始嫌弃聚会的小后生们牢骚多闲话多。她循循善诱,劝导他还是少跟这些人聚会“国家大事那都是公家的事儿,能随意评说、胡说八道吗,祸从口出,狂言不逊只能给自个儿跟家人招祸,没甚用项。”瞅着说了几次,见说不动丈夫,她就转变策略,天天唠叨早点回去,说出来久了,怕家里人担心。张申本就觉得西安的气氛不是很对路,也就听婆姨的话,灰心丧气回去了“没教导成婆姨,反倒叫婆姨上了一课。”无语的张申回到镇北,沉默了很长时间,也没了聚会的心情,只是有空去铺子找女人聊聊,舒缓放松一下枯寂的心。女人劝他去重庆看看,那里可能会找到出路。张申打定主意,没多久就安顿好大肚子婆姨,只留下一封给家人的信,一个人不告而别去了重庆。
榆生回来了。上海沦陷后,生意买卖一落千丈,那个妖冶的女人眼瞅着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紧巴,没打个招呼就勾搭上个野男人跑香港去了,这还是他四处打问才弄明白、搞清楚的。榆生没了心劲,商路断了,少掌柜走了,他在上海也没甚好做上的,老掌柜来信说“能做点甚做点甚,不行,就回来吧。”榆生思前想后,不再留恋这个热闹非凡的花花世界,把能卖的都卖了,换成金条,卖不了的就送人了事儿。拾掇好摊子,他就打包好行李,一路走走停停,赶回了镇北。路上到处都是逃难的人,一拨跟着一拨,跟着行色匆匆的难民,他一路不停歇地往北走,好几个月才回到镇北。
瞅着灰头土脸、衣衫褴褛的榆生,大家伙儿唏嘘不已。刘老爷子说“回来就好,人没事就好。兰子,拾掇个屋子,安顿好榆生,吃好喝好再来拉话。赶紧的。”榆生安顿下来,跟掌柜的交待好事儿,把带回来的金条也说清楚来龙去脉。刘老爷子叫婆姨收好“你先歇几天,过一阵子,身子养好了,就到铺子里帮忙。”
榆生在大院住了下来,闲来无事,没几天就跟槐花混熟了,有了些意思。女人看出些端倪,觉得两人挺般配的,私下里跟两人探了探口气“郎有情妾有意,这事妥了。”她跟爹娘商量了一下,老两口都说这事挺好。女人打人去庄子把两家的老人叫来,跟公婆吃喝了一顿,老人们好商好量就把事儿定了。两人在金鸡滩都有家有老人,婚事自然有老人、兄弟们操心料理。榆生跟槐花成亲以后,还在大院住着,各自还是干以前的那些生活,小日子过得和和美美的。
眼瞅着挂在墙上的一幅幅照片,女人又想起她跟男娃在一起的美好时光“墙上的这些照片记录着我们的过往,每一张都是一个故事,一段情话。那时候,志趣相投的我们沉浸在书的世界里,每天都有拉不完的话。书里那些美好的词句,无形中都在一点一点投射到我们的身上跟心里。虽说成亲了,我们却仿佛怀春的少男少女,在谈一场羞涩甜蜜的恋爱,彼此小心地去触碰对方的身体跟灵魂。我们细细品味书中描绘的意境,临摹着书中描绘的情状,仿佛扮演着不同角色过家家,在角色的扮演中投入情感,体会那些淡淡的哀愁忧伤,淡淡的舒爽畅快,享受那份如烟如雾的惬意。在平淡如水的温存中,我们走进了彼此的心里,持久地升温彼此的情感。我们没有感天动地的爱恨情仇,也没有花前月下的海誓山盟,有的只是一份依恋,一份理解,一份共情。我们小时候都过着富足、随性的生活,并没有真正经历过世间的尔虞我诈,见识过现实的冰冷残酷,依然保持着心灵的那份纯净。你为人温和豁达,我做事随意率性,我们仿佛是从西方童话中走出来的王子与公主,东方神话中走出来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眷侣。我虽说伶牙俐齿些,也就是嘴上的功夫,叫我去算计人,那也是做不了、做不到、做不成的。你就更别说了,一心向往自由自在生活的你,被爹从小到大呵护的很好,根本理解不了,也接受不了,那些生活中无处不在的阴暗、丑陋、肮脏。我们的脑子里没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只是凭着天赋、天性在书写的人生。世间惯常的那些,好些在我们的眼里都不屑一顾,视若无睹。我们相识、相知、相依、相偎、相恋、相爱。可你为什么一个人走了,那么义无返顾。为什么不等等我,带上我。为什么我去找你,你却视而不见。我想跟你永远在一起,你不是说我们永远不离不弃的吗。”
她想着想着就想出了神,望着映照在窗户上隐隐绰绰的影子,夜还是那么静,那么冷清,她提笔在桌上摊开的纸笺上写了几句“竹影蝉鸣窗纱,晚风细雨兰花,寒池幽径篱笆,远山如画,倚门盼君回家。”
闲来无事,刘瑞最近喜欢上大院走走,不为别的,就想跟枣花拉拉话“枣花长大了,女大十八变,出落得条正貌美。大眼睛忽闪忽闪的,大奶子一晃一晃的,大屁股一扭一扭的,浑身散着春天的味道。勾得人心里猫抓一样,一愣一愣的,眼睛都直的,裤档都差点顶起来。所幸穿得是长袍大褂,不然可就丢人现眼了。”
枣花心里有了些异样的想法,对他献的殷情那是照单全收,见到他眼睛里能挤出水来。郎情妾意,没过多久,两人就好上了。刘瑞好吃的、好穿的、好戴的送了枣花不老少,可就是只字未提娶她过门的事儿。枣花每次欢好后,都眼泪汪汪的撒娇卖乖,旁敲侧击叫刘瑞娶她过门,生怕时间长了怀上了咋办。刘瑞每次都甜言蜜语说“忙过这一阵子,我就跟爹提这事儿,正儿八经、八抬大轿,去金鸡滩接你过门。”
慢慢的,枣花现刘瑞来大院寻她的次数越来越少了,就起了疑心。有天傍晚,她瞅见刘瑞进了大院,去堂屋跟爹拉完事儿,也没来见她,就急匆匆走了。枣花跟春花打个招呼“有点事儿,要上街上走一趟。”她忙活撩乱出了大院,远远瞅见刘瑞拐过巷口。她赶紧溜边跟上去,尾随了好一阵了。刘瑞走到街上,走了老长一段,拐进了一条巷子,七拐八拐进了一个小院。
刘瑞进了小院,关上门一直没出来。过了一阵,院子里就传来女人脆生生的笑声。天黑下来,屋里点上了灯,屋子里一片光亮。枣花从大门的缝隙往里瞅,窗户纸上隐隐约约映出两个人影,两个人影正在屋子里嘻笑打闹。枣花胸腹间腾地冒出一股心火,火苗越烧越旺,烧得她头昏脑胀,火冒三丈。怒从心头起,枣花咚咚咚地向力敲门,一声也不吭。没一会儿,她就听见刘瑞出门问“谁呀。”她也不吭声,只是一个劲捶门。刘瑞正情热意浓,被耽误了好事,骂骂咧咧出来“驴日下的,哪个王八蛋想死不找好地方,看老子不捶死你个驴日的。”打开大门,刘瑞看见是枣花,故作镇定说“你咋寻来的,来作甚,有空我会去找你。没事回去吧,小心人瞅见。”枣花泪流满面,边撕抓刘瑞,边哭着骂道“你个没良心的,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你今儿个不给个说法,老娘打不死那个骚情货。我说最近咋不来找我,原来是又有了相好的,把我撂一边了。”骂着骂着,她就往屋子里走。进了屋子,她正好瞅见一个描眉画线的妖冶女子,头散乱地在炕上往身上套衣裳。她气更不打一处来,也不脱鞋,一猛子跳上炕,撕抓那女子。那女子也不是省油的灯,使劲用手撕抓、用脚狠踹枣花。两人从炕上撕打着滚到地上,那女人吼喊刘瑞“死人啊,还在那里干站着做甚。不把这个泼妇除灭了,我现在就走。看你个怂囊包,作下的甚事。哎呦,老娘跟你拼了。”恶向胆边生,刘瑞正恋奸情热,从灶房拿了根擀面杖,用力朝枣花头上来了两下。枣花应声倒地,血流了一地,没了声息。
刘瑞冷静下来,晓得出人命了,吓得不轻,哆哆嗦嗦地跟妖冶女子说“小翠,咋办呀。”妖冶女子倒是镇定“去弄辆马车,弄个麻袋,趁夜拉到城外埋了。神不知,鬼不觉,有谁能晓得。”
刘瑞照着相好的说下的话,出去了一趟。回来他就瞅见脚地上已经清理了一遍,没甚血迹了。两人相帮着,把枣花装进麻袋里,抬上车。刘瑞一个人赶着马车,趁着夜色出了城。他赶到一处熟悉的山坳,拿出铁铁锨刨了个深坑,把麻袋扔进去,填上土埋好,用脚踩实,铲了些别处的土洒上。朦胧月色映照之下,山坳还能大概看清楚。他四处瞅了一遍,没现什么异常,才觉出了一身汗。他赶紧赶着马车往回走,一路提心吊胆就怕碰上人“还好,还好,一路顺风回来了。”他又跟相好的把里里外外拾掇了一遍,才忐忑不安地睡下。
第二天,刘瑞乖乖地上铺子照应,也不训斥伙计们了,只是一个人在那儿呆,抽闷烟。过了几天,他听伙计们私下里议论,有伙计说“大院里的人找不到枣花,老掌柜就跟公家报了案,又跟枣花他家人说了,找了这么些天,也不见个人影。是不是瞅上哪个小后生,跟人跑了。”有伙计说“哪可能,要走也会跟少奶奶打了招呼的,哪象如今,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有伙计说“那可说不准,如今的女子,胆子可大了。”有伙计说“枣花瞅着挺乖巧的,没可能跟人私奔的。”这天下就没有不透风的墙。大家伙儿心知肚明,早晓得枣花跟小掌柜好上了,如今枣花不见了,看他不着急,又不敢吭声,私下里背着他嘀咕“小掌柜咋跟个没事人似的,这事儿家里都挺着急的。少奶奶天天去公家那儿打问情况,跟四邻八舍都打问遍了,也没个准信,人就这么不明不白不见了。这世道啊,是越来越乱了。这几天公家人上门,把家里的所有人都盘问了一遍。小掌柜没事人似的,只说不晓得,没见过,也不晓得是真不晓得,还是假不晓得。可惜死的,多栓整的一个女子,谁讨回去做婆姨不成,也不晓得便宜哪家后生了。”刘瑞一口否认跟枣花相好过“就是口花花骚情了几次,私底下没甚来往,两人清清白白的。谁晓得她跟谁相好上了,说不定早跟人跑了,现在指不定在哪儿快活呢。”公家人调查了一阵,就不了了之,草草了事了。刘老爷子全当啥也不明白、不清楚,好生安抚了安抚枣花家的人,说往后大家都留意着找寻枣花,别着急,给了些银钱打了“家里头的明白人都晓得,这事跟二小子脱不了干系。可胳膊肘往外拐的事不是人干的,大家伙儿都揣着明白装糊涂呢。枣花才多大啊,就这么不明不白不见了,可惜了。可又能咋办吗,如今只有这么一个顶门立户的狗东西。那个灰小子咋还不回来,是死是活,来个信也好吗。”一个正值青春,花一样的女子,就这么无声无息,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乱世人命贱如狗,穷苦人活得不如狗,由此可见一斑。活着的人各有各的活法,谁又晓得是非对错呢。
女人一大早起来就开始忙活“今儿个过中秋,林子不在,过节采买瓜果就要我这个儿媳妇操心了。”她侍应公婆吃过早饭,就叫上春花、强子往菜市场走。路过莲花池,她顺道想瞅瞅残荷、秋水“前几日写了点儿小文章,似乎缺点什么。”她依着垂柳立在水边“池水很清澈,小野鱼在池中随意的游动,时隐时现。浮萍与细草在微风的吹拂下,轻柔的晃动。柳叶已经有些枯黄,开始向大地上飘落。柳条不再象春天那么细柔,韧性倒更足了些。这个季节从树上采下的柳条又长又粗,正适合编筐,没有太多水份,也不象冬天那么干硬,编出来的筐最结实。可以想见,这时候庄子里的农家正从树上割些柳条下来编筐。真是一个收获的季节,瓜黄果红稻香飘,荞麦花开赛梨桃。再过个把月,镇北就上冻了,男人们就开始真正过起婆姨娃娃热炕头,划拳喝酒闲聊天的日子。我也可以多念点书,多写点字。绣坊也要忙活起来赶冬衣,好在年前腊月卖出去。镇北人再穷,也要在腊月给婆姨娃娃置办件新衣裳,图个吉利,讨个彩头,面子上也过得去,不能叫四邻、街坊看了笑话。”
女人正在那赏景愣神,远处就传来嗡嗡的轰鸣声。不晓得谁喊了一嗓子“飞机来炸人了,快跑啊。”
喜欢风往北吹请大家收藏风往北吹本站更新度全网最快。
老兵新警
文案不想退役时脱下了军装。从未奢望过能成为警察竟穿上了警服。下定决心扎根边境坚守国门,却又被调回了老家。命运就是这么奇妙,且看韩昕从橄榄绿到藏青蓝的精彩人生!...
漫威神豪血神
设计成为吸血鬼的血神之后,主角发现,自己不仅拥有了不死的能力,还拥有了比托尼斯塔克更加丰厚的身家!...
碰到异类就变强
gtp1tgtdivnetkquot1tgtahrefquotbeginquot1t立即阅读gta1t...
狂飙吧!赘婿
简介关于狂飙吧!赘婿着重强调(并非出轨绿帽文,前期是有些脏。拥有精神洁癖的人勿入坑。作者素质比较低你要是指出不足会接受,恶意说有的没的真不好意)常年在外执行任务被注入不明药物剩下的时日不多,回到都市被昔日恩人上门要挟娶他女儿,本以为对方惨不忍睹厂家才会着急清仓,没想到是个美人儿。两个没有感情的人婚后签订互不相干协议,婚后半年妻子前男友回国,醉酒进入酒店被娱乐记者偷拍爆料,曹恒不想继续再演下去,坚持离婚。离婚后,三番两次的巧合救下假结婚的前妻大家可以耐心看完人物塑造再评论或者要不要再继续看下去。不要一来就说女主太差劲差评,这世道哪有如蒸馏水一样干净的人。(故事纯属虚构,请勿角色代入。)...
辣妻当道,撩最野的汉生最靓的崽
6一依前世是个恋爱脑,被敌蜜跟渣男咬着吸血,哄骗她婚礼当日私奔,让她衣不蔽体出现在众宾客面前,名声尽毁!又以她的名义毒杀她父母侵占家产,害她死不瞑目!幸好,老天爷让她回到新婚那一日!宋清扬带她私奔那一刻!重生归来,她誓要让那些害过他们的人,全都付出惨痛的代价!她费心筹谋,改变命运,只是那军中阎王为何死缠着自己不放。顾淮序,您说什么?我说,你这次忙完出差回来,再给我生个可爱的闺女。大家都说,顾淮序娶了个丧门星,婚前跟人不清不楚,这婚迟早要离!可没想到,他们不仅没离,偶尔还斗斗极品,虐虐渣滓,孩子更是一次来仨,小日子还越过越红火。...
摄政王的农家小福妻
简介关于摄政王的农家小福妻大旱三年,颗粒无收,百姓在生死边缘苦苦挣扎。姚家有女,身负重伤,奄奄一息。一群人等着分而食之现代女孩,五星级大厨姚灵穿越来了,击退恶人。捡到一个病娇男人,附带小正太,从此深处绝境的姚家人过上了顿顿吃肉,穿新衣,建大房子,数钱数到手软的日子。听说摄政王的夫人是个粗鲁的乡下人,一顿能干两碗饭。小皇帝谁在编排我舅娘,拉出去砍了。年轻的摄政王温柔的道宏儿,这样不好。来人,拖下去饿上七天七夜。小皇帝姚灵别闹了,我要数钱钱。...